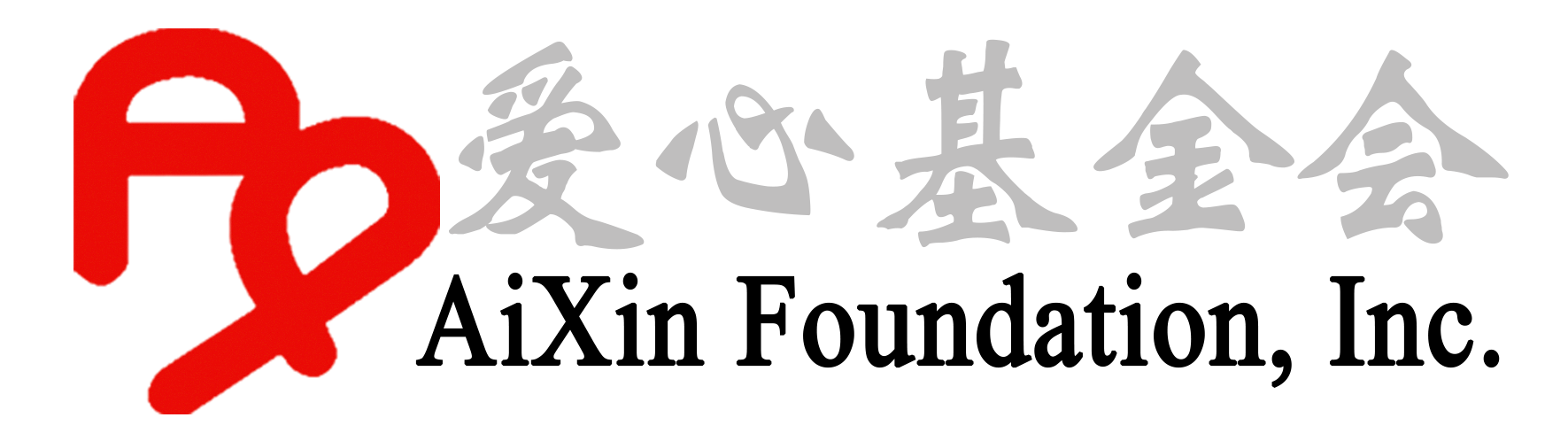乡村医生现状与面临的难题
编者按:在农业社会,乡村医生曾是全村羡慕的职业。但如今,徘徊在医疗体制边缘外的村医已经吸引不了年轻一代。一个村医要照顾承担全村的医疗与照护,庞大的工作量让许多人无法承受,选择离乡务工。近5年,村医数量正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有人觉得村医没地位,收入低没前途,后继无人的现状令人忧心。
作者: 邱慧 中国慈善家杂志 編輯:愛心志願者
骑马村医
李玉忠是半路出家的乡村医生,十多年来,村子只有他这一位乡村医生照看这里2741人的健康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玉忠初中毕业回到村里。父母瘫痪,姐姐是残疾人。当时李玉忠最常做的事就是去村卫生室,叫上年轻的女村医来给家人看病。后来村民投票选他当村长,负责村子里的大小事务。怕耽误家人看病,于是他开始自学医学知识。2005年他去州里的卫生局学习一年、实习半年后回乡时,村里唯一的村医辞职进城,36岁的李玉忠便接替了她的工作。
村医要做的事情很多,打针、输液、处理打架村民的伤口……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不了卫生室,还得上门出诊。碧播村紧邻中越边境,四周环山,寨子间相隔较远,有的不通路。想到村民家,李玉忠得背着药箱翻过山头。山路崎岖,七八公里的路得走上两个多小时。
早些年,村子没通电,药箱里的疫苗得不到低温保存,只能靠路上加速节省时间。村里的老人见他翻山越岭不容易,建议他买匹马代步。买马是笔大花销。小马驹4600元,接近李玉忠当时月工资的40倍,他找外出务工的朋友借钱买了一匹。久而久之,寨子里的村民听到悠悠的马蹄声也能猜出个大概——李医生骑着马来了。再后来,村子里的人都称呼他“骑马医生”。
身份难题
村医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要寨子里来了电话就得出发。为了能接到电话,李玉忠拿出存款买了部手机,整夜开机。有一次凌晨一点,手机响了,哈尼族寨子里的一位村民病了。他背着药箱走了一个多小时,去给病人打针。路上花了将近3个小时,一针才收费3元。 钱不多,但心里满足。
李玉忠记得刚当乡村医生的头两年,只要有病人打电话,自己就很激动。那是一种被认可、被需要的感觉。当村医的第三年,最远的寨子打来电话,一位产妇要生了。李玉忠没接生过,只能求助乡卫生院院长,通过电话指导,帮产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李玉忠行医经历丰富,但他也说不清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医生,只是以“赤脚医生”自我打趣——这是“乡村医生”的前身。
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医疗资源匮乏问题,鼓励医疗资源下乡,为乡村提供基础医疗体系。由于医学专业人才稀缺,只能培训一批粗通医术的人应急。李玉忠说,当了十几年“没有名分”的村医,他从没后悔过。当村医的第一个月,他领了30元的工资,同乡出去打工的兄弟一个月能挣180元。妻子劝他也出去闯闯,他不干,他对治病救人有着“解释不清”的热情。
当上村医后,李玉忠读了医学中专。碰上公益机构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他也想办法报名参加。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仍不是正规军。在全国,像李玉忠这样的乡村医生有79.2万名。他们身着白大褂行医,承担着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这些“李玉忠们”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半农半医”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提到,村医中70%左右为中专文凭,过半村医没有任何职称。“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驻点队员队长郭帅跟村医打交道4年,走访过200多名村医。他发现,近几年考资格证书的村医越来越多,但多在取得资格证书后就离开乡村,转至乡卫生院或县级医院工作,村里留下的多是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村医。
郭帅说,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医面临无编制、无社保、退休后还是农民待遇的窘境。调查数据显示,仅26%的村医有养老保险,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500元的占43.76%。还有19.82%的村医每月养老金额在100元以下。
” 消失”的村医
今年25岁的钟丽萍是云南澜沧酒井乡岩因村的村医。2012年起,多地推行每一千名农村户籍人口配备一名乡村医生。岩因村1868人,需配备两名医生。外地人不愿意来,原在县城上班的她回到村卫生室担任村医。在村里,学过医同时还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年轻人只有钟丽萍一个。8个寨子里150余位老人一季度得上门随访一次。6位精神障碍人士、5位糖尿病患者、131位高血压患者,至少每月上门查看一次。
钟丽萍说,村医不仅要给村民问诊,还负责全村的公共卫生。2016年,国家发文,提出2020年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落实到乡村,就意味着村里的幼儿健康管理、孕妇建档、村民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由村医统一收集信息,做好信息录入工作,并定期去乡里、县里汇报。钟丽萍坦言,开会、做表之类的行政工作占据了村医一半以上的工作精力。卫生室七点半开门,但村民不到七点就会敲响卫生室的大门。最多的时候一天30个患者轮番候诊。“哪儿还有时间深造。”钟丽萍叹了口气。
后继无人
《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近5年,村医数量在以平均每年5万的速度锐减。 李玉忠也发愁:等到自己退了休,谁来接替他的工作?郭帅认为,若不明确村医的身份问题、提高收入,这个行业很难注入新的血液。目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诊疗费以及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三部分都算上,钟丽萍能拿到3000元左右,偶尔遇上“上级”发不出工资时,一月一发的工资自动改成了两个月一发。
看着同学都去了城市,钟丽萍也在犹豫要不要进城务工。但她也纠结,村里不通汉语的老人因沟通问题难以外出就医,多是选择在村里卫生室就诊。逢到自己有事外出,卫生室关了门,老人们就忍着,等她回来了再看。“如果我走了,这里更没有人来了。” 钟丽萍说。
后记:
爱心基金会衷心感谢来自美中两国爱心人士与志愿者的无私捐助和奉献支持。
爱心基金会享有美国联邦政府501(c)(3)免税待遇和美国联邦政府联合捐款(CFC # 10769),如您有意支持中国农村的爱心助学和健康教育,中美文化交流及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项目等,爱心基金会将全力助您达成心愿。
如欲了解爱心基金会,请浏览爱心网页: www.aixinfund.org
如欲联系爱心基金会,可Email: aixinfund@gmail.com
或致电Tel: (202)-321-8558 张伊立博士 / (301)-529-9419 高放先生
您的善款支票可寄往:
AiXin Foundation, Inc., 13621 Valley Oak Circle, Rockville, MD 2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