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校长和学生们:高考面前,想留得住更想走得远(上)
编者按:2024年5月最后一天,还有一周就是高考,云南省红河州47位县域中小学校长,却离开了学校和学生。他们集结到清华园,参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主办的“弦歌不辍,厚德树人——助力山区校长公益计划”,他们背着山区教育的困局来,努力寻找破局的路子。凤凰网公益对话了几位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南部边疆县域高中的校长。这一期,我们就去了解他们的教育探索和理想。
转自:凤凰网公益频道 作者:李迅琦 编辑:爱心志愿者
据统计,中国两千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仅从数量级上看,县域学生的教育就关乎国家未来。校长们的成就与困顿共同构成一份对山区县域教育的观察样本。他们试着回应了一连串仍需时间验证的问题:县中孩子们的处境变了吗?不做“小镇做题家”,他们还有什么可能?
校长去哪了
红河州教体局教科所负责人介绍,红河州的高考成绩在云南省内大概排在第三名左右。但在红河州内,北部七县与南部六县差距巨大。南部六县市(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屏边、河口)反映教育质量的“三率”数据(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大多低于红河州均值,也因此成为国家教育帮扶的重要对象。
绿春县高级中学的副校长白礼华和红河县第一中学的副校长姚薇都是本地人。他俩都从基层教师成长起来,二十余年的教育生涯里,本地的风土连同问题一同长进骨血。
元阳高级中学的副校长吴闯是曲靖市宣威人,出身云南省内的教育高地,2022年与上海来的帮扶校长来到元阳高级中学组建新的校领导班子推动改革,35岁就成为校党委书记。曾带着家乡的标准审视这里,直到栽了跟头。
屏边一中的副校长曾长春曾在上海位育中学教书十年,是这批校长群体中的例外。他2004年曾来屏边支边,去年从北部的知名老校蒙自一中再次回来任教,他觉得自己“回家了”。最后的十年,他想在这里实现些什么。
然而,无论对哪位校长而言,面对困局,想要破局实在不容易。
生源问题首当其冲。“每年升到我们这里的学生,中考总分700,很多录取分数只有两百多分。”吴闯介绍说。
“难”是面临相似情况的白礼华的处境,他说:“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从小习惯说方言,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就变得很困难。”缺乏能激发学习效仿的“鲶鱼”,学生们感到自己不被期待,也看不到往上走的“榜样”,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存在中途退学情绪。
还有始终缺位的“家校共建”。为了挣得盖好房子的本钱,年轻的父母们早早前往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留下幼小的子女和老人生活。缺乏情感的关照,边疆山区县域高中的孩子们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上问题重重,这就使得老师们在教学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学生情感养育的职能。
为方便随时了解孩子们的身心状况,曾长春至今住在学生宿舍,他要和上课打瞌睡的孩子谈话,寻找生日当天离校出走的同学……白礼华苦于寻找让教育帮扶真正落地融合的法子,绿春县高级中学至今已经接受了来自不同地区帮扶,但如何让教育模式停止“拿来主义”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红河县一中副校长姚薇和元阳县高级中学的副校长吴闯,为了把厌学的孩子“先留在校园里”,他们把课堂拓展到教室外,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如何深化效果,是两个人都在面对的挑战。
眼下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是校长们要翻越的又一座大山。他们觉得“短期之内,工作更难做了。”
县中的师生,一种处境
一直以来,围绕在县中师生之间的,是一种被“卡住”的情绪——走不出去,留不下来。
根据几位校长的说法,在红河州南部的考生群体里,普通高考、艺体特长、定向招生是最主要的三条路线。除了艺体生,学生们填报志愿的首选专业通常是师范、医学、计算机、汽车维修,因为稳定、强技能、好找工作,方便回来,“真正出省的还是少数”。
走出去的孩子怎么样了?
李开光,是曾长春2005年在屏边支教时的学生,目前在上海从事公募基金工作,是少有的从红河谷“走出去”的学生。当年上海徐汇区定点帮扶云南省屏边县,可以让一位山区学生到上海上高中。在曾长春的争取下,家庭贫困的李开光凭借优秀的成绩得到了让人眼红的机会。最后,李开光在大学期间选择了家里人没什么概念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学”。如今,李开光奋斗十余年,终于在上海扎下根来。他过得更好了吗?因为金融业的工作,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但还是要面对疯涨的房价。
留下来的孩子怎么样了?
曾长春的另一位学生叫陶映江,大学考入了云南省师范大学,毕业时也有机会留在省会任教,但因为“不想留妈妈一个人”在家,她回到了屏边一中任教,今年带这一届高三毕业班。她有机会用自己的所学,影响和她一样的孩子。作为二十年前考出去的县中孩子,姚薇和她做了相似选择。在白礼华的学校,这样的情况更是普遍,“和我共事的有六个都是我带过的学生”。
哪一种选择更好?尤其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县域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走出去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吗?
“你希望你的学生走出去还是留下来?”每一个校长听到这个问题,都选择了前者,“至少要先看看世界,再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他们也秉持另一个信念——“我们培养学生,不是为了让他逃离家乡,而是为了让他建设家乡”。(未完待续)
后记:
爱心基金会衷心感谢来自美、中两国爱心人士与志愿者的无私捐助和奉献支持。
爱心基金会享有美国联邦政府501(c)(3)免税待遇和美国联邦政府联合捐款(CFC # 10769),如您有意支持中国农村的爱心助学和健康教育,中美文化交流及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项目等,爱心基金会将全力助您达成心愿。
如欲了解爱心基金会,请浏览爱心网页: www.aixinfund.org
如欲联系爱心基金会,可Email: aixinfund@gmail.com
或致电Tel: (202)-321-8558 张伊立博士 / (301)-529-9419 高放先生
您的善款支票可寄往:
AiXin Foundation, Inc., 13621 Valley Oak Circle, Rockville, MD 20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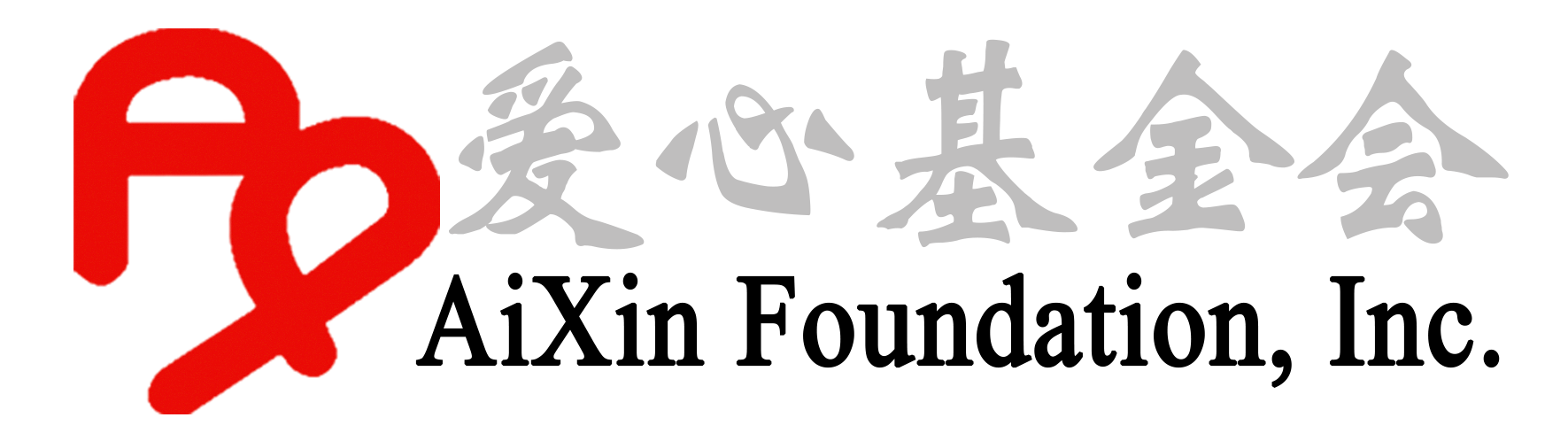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