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破坏的珍宝,她用一辈子来守护(上)
编辑按: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莫高窟周围,围绕着一代代的工作者:修文物的人、讲解员、技术人员等。在他们到来前,莫高窟不过是一片沙土堆积的断壁残垣和危险楼阁。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边做边摸索,她也走上了一生在戈壁守候莫高窟的道路。
作者:黄靖芳/南风窗记者 编辑:爱心志愿者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莫高窟南区准备启动加固工程,正需要一些专业的考古学生协助发掘。对年轻的考古系学生来说,莫高窟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艺术宝库,人人心向往之。
当时24岁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被选中前去实习。初次进入洞窟,温度比室外还要低得多,樊锦诗看着洞窟里色彩斑斓的壁画,把寒冷忘记了。从北魏到隋唐,从女娲到飞天,满天的壁画犹如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
上海长大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虽然满心欢喜,但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实习结束后,当她被正式分配到敦煌工作后,但父亲担心她的身体,写信给学校领导希望改派分配。
樊锦诗偷偷拦下了这封信,她不希望搬出父亲来说情,她接受了分配决定。孤寂辽远的莫高窟长期被风沙包裹。在毕业后的55年时间里,樊锦诗远离了繁华又喧嚣的都市,在大漠里成就自己的事业。
用笨方法来传承
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洞窟的分布高低错落,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公元366年,一名僧人路经鸣沙山,看到这里有金光闪耀,于是在岩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
多年之后,丝绸路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官员、百姓、财主、士绅为了积功行德,都纷纷来开凿佛洞、塑佛像、画壁画,一个个洞窟营造起来,从无到有,千年的时间里,让这片断崖成为了万佛之国。
常年的风沙洗礼,带给了莫高窟独特的历史面貌,也塑造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来到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并开始修建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但是,敦煌没有土,只有沙,他在商贩那里学到方法,“用含碱量大的水混合沙土,使劲夯,就能筑成墙”。有了这堵两米高的土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就这么笨拙但仔细地展开了。融合了中国和西域的佛教文化艺术的宝库莫高窟,被如此冷落在荒凉的境遇里。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常书鸿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希望他们亲自推荐和招聘愿意来敦煌的年轻人。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来到了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是常书鸿的学生。后来,也有“门外汉”来到。
少年的樊锦诗在洞窟里碰到了工匠李云鹤。李云鹤是一名山东青州的农民,带着几个伙伴准备到新疆种棉花去,路过敦煌,想到莫高窟拜拜菩萨,结果遇到了常书鸿。常书鸿一再劝说,把他留了下来。
李云鹤干活勤恳,他原本以为在莫高窟的工作是一些体力活——把洞窟里的积沙扫出来,堆到窟崖下面,再用车拉走;这些工作他干起来很勤快,但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打算交给他专业的修复保护工作。
年久失修的莫高窟壁画表面,出现了起甲、空鼓等现象。起甲是壁画上出现了像鱼鳞一样的龟裂,空鼓则是因壁画和墙面之间存在空气,敲起来有咚咚的声音,两者都算是“病害”。
外国的专家为此专门来过莫高窟,在现场演示了一种“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很适合壁画的修复。李云鹤在旁边观察得很认真,专家走后,他试着用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制成黏接剂,再用针管顺着起甲壁画的边缘沿缝隙滴入、渗透进去,等到壁画表面水分变干,他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确保粘贴得牢固。
当时,国内对莫高窟这样的洞窟进行壁画修复的科学方法,仍是一大片空白,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是李云鹤在往后的数十年里边摸索边改进:针管太粗了,他换成气囊;纱布有纹路,他改成了纺绸,在这样的探索下,李云鹤逐渐成为了著名的壁画修复专家,成为中国文物修复界的泰斗。
樊锦诗在自传里感慨地说,“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边干边摸索”。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宿命感,樊锦诗沿袭了这样的心性和精神,她也跟着走上了保护莫高窟的道路。
为了留下莫高窟
樊锦诗最初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的老师——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对她寄予了一个希望:完成莫高窟的考古报告。
古代的文物遗迹历经久远,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发掘保护下,它们能延长寿命,但很难阻挡其退化的趋势,莫高窟也不例外。“即使有一天石窟不在了,人们也可以根据考古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石窟进行精准复原”,这是考古学界人士对莫高窟考古报告设立的祈愿。
在另一部名为《敦煌师父》的纪录片里,记录了敦煌研究院里的师父和徒弟们的故事。其中一集的主角是浙江大学的考古学硕士张小杨,她是考古研究所的新一代年轻人。工作里,她被分配到完成第254窟考古报告的任务。
这个任务难倒了她。考古报告需要对洞窟整体结构和所有壁画细节进行详细记录,254窟是莫高窟开凿时间较早的洞窟之一,壁画存在着烟熏、脱落、破损的问题,很多地方模糊难辨,何况,“一千个形态不同的佛菩萨,就要经过一千次辨识、考证与记录。”壁画烙下了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风格,需要记录者耐心地了解和厘清背后的历史意义。
单是一个洞窟的考古报告的困难程度是如此,整个莫高窟考古状况的难度可想而知。(未完待续)
后记:
爱心基金会衷心感谢来自美中两国爱心人士与志愿者的无私捐助和奉献支持。
爱心基金会享有美国联邦政府501(c)(3)免税待遇和美国联邦政府联合捐款(CFC # 10769),如您有意支持中国农村的爱心助学和健康教育,中美文化交流及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项目等,爱心基金会将全力助您达成心愿。
如欲了解爱心基金会,请浏览爱心网页: www.aixinfund.org
如欲联系爱心基金会,可Email: aixinfund@gmail.com
或致电Tel: (202)-321-8558 张伊立博士 / (301)-529-9419 高放先生
您的善款支票可寄往:
AiXin Foundation, Inc., 13621 Valley Oak Circle, Rockville, MD 20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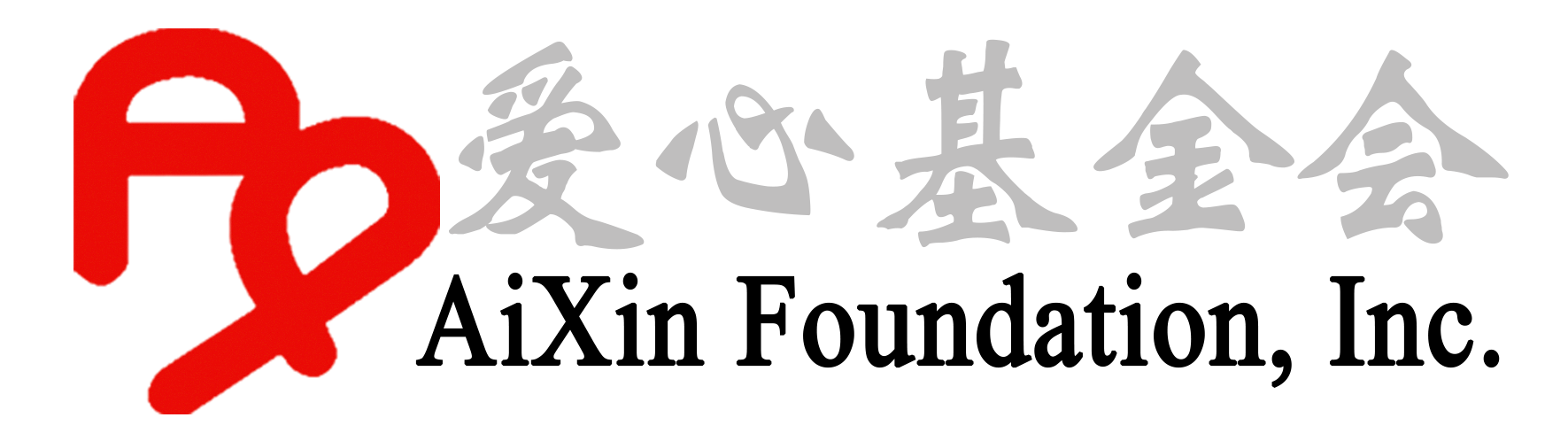
在敦煌工作.png)

